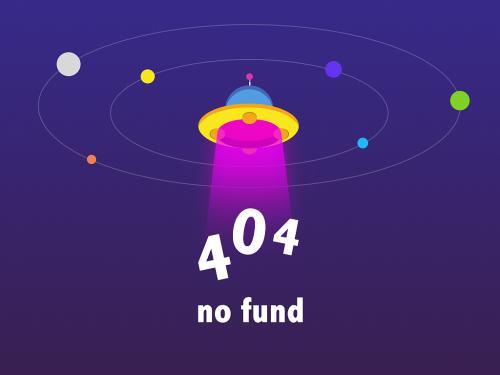导言: 来源: 作者:peeter vihma 编译:智政院 「进入本世纪20年代之际正是一个总结前车之鉴和优秀经验,继往开来的好机会。」[1]两位数字革新研究者在其最近的共同研究中将爱沙尼亚数字政府的成就归功于「无畏」。 伦敦大学学院的rainer kattel教授和康斯坦茨大学的ines mergel教授引用了爱沙尼亚独立后首任总理mart laar在激进地推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自白:「彼时我不过32岁,国家百废待兴,什么事能成,什么事成不了只有天知道,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又为何不去放手一搏呢?」 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局决定对苏联时期数字遗产进行松绑,避免了对旧有信息化和数字化部门与设施的续命沿用,从而创造了「技术跃迁」的良机。mart laar回忆起当他出任首届总理之后不久,办公桌上就送来了塔林科技大学的计算机工程教授raimund ubar提交的备忘录,立场坚定地建议一定要规避很多西方国家走过的「受遗产包袱所累」的数字化道路。备忘录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写道,「破旧而立新。」 这是一次从各种意义上的全新征程。作为欧洲最年轻化的内阁之一,laar和他的那些资历尚浅的内阁成员们可谓白手起家,他们肩负以有限预算和紧迫周期完成国家体系重新正常运转的重任。kattel and mergel教授认为,laar内阁的冒险主义精神源于他们的年轻无畏,这种精神引领他们构想并推行一种「使it建设对公众具备普惠意义,以发挥通用社会经济功能为核心」的公共数字基础架构。 隐藏的手和政治决策 古训有云,成王败寇。在既定成就的背景下,事后诸葛亮式地去解释爱沙尼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然而经济和政策领域的学者们长期以来的研究一直试图提醒我们,成功的革新并不完全来自预期。kattel和mergel教授没有按照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套用「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解释爱沙尼亚的数字化转型,而是套用「隐藏的手」理论来解释。「隐藏的手」理论由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alberthirschman在1960年代提出,他认为「创新永远同我们不期而遇」,也就是说人们只有被「隐藏的手」遮蔽了视线,对行动可能导致的困难和苦果无知无畏时,才能不患得患失地激发创新精神。 最近随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声名鹊起,这种观点得到了更多论证和支持。早期理论模型大多偏爱于应用渐进法则。当政治家和人民公仆们希望进行政策改革时,他们首先分析问题所在,继而构想多种ag凯发k8国际的解决方案,一一进行评估并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作为最终对策。然而行为主义认为,人(在更多情况下)的选择并非那么理性,我们的判断实质上往往只是来自于试错法、个人经验、偏见和一时的情绪。因而政治决策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认为「现在社会,决策时最主要的障碍并非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导致的犹豫踌躇)」[2],因此决策更多时候应该是一种包容性的对创新的「快速试错」,而不是浪费太多时间去将论证做到万事具备。就拿2009-2010年的欧债危机来说,这种快速的决策和变革成为了各应对危机的一种本能反应[3],没有任何国家事前规划过颠覆性变革,但是当危机发生之时,各国的变革如一场场令人目不暇接的即兴演奏一般随之而来。 在「敏捷化政策演进」[4]以及「政策制定试点」[5]的理论当中同样遵循这种逻辑,这两个理论也非常强调在公共政策设计时要注重解决紧迫性问题、小规模试点和快速反馈。因此我们可以说,当缺少外部因素(比如欧债危机催生的种种)来驱动紧迫性需求的产生时,我们自身应当有意识地创造某种紧迫性需求。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不是说传统决策方式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而是随着锚点的改变,它自身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以示反馈。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有着「说干就干」的豪迈就必然能够成事。例如在hirschman自己的论述[6]中也提到,以对很多发展项目的统计结果而言,仅有22%的项目从「隐藏的手」对困难预期的遮掩中受益,而剩余78%的项目由于失败的规划蒙受损失。「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但骆驼的缰绳定要栓紧。」这句格言教导我们,成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互信为基础的关系网络 kattel 和mergel认为,爱沙尼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全国公有和私有部门成员间形成了无数个高度自觉和关系紧密的小型关系网络。这种情况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独立之时,爱沙尼亚已经穷到近乎国家破产的程度,国家事实上无力承担大型中心化国家数字体系的建设方式。因此政府某种程度上是被逼无奈地尝试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体系架构,以满足各政府机构的多样化需求。这促成了很多与私有部门的合作共建,例如与银行系统共建数字安全体系。 kattel 和mergel特地指出,政企合作的方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当中往往缺少信任土壤。担心贪污腐败和事后追责等问题导致这种合作如履薄冰,因此如何正确促成这样的合作关系向来都是一个巨大挑战。在上文中,我提到了小规模试点和达成紧迫需求共识,这都是可能的催化因素。对国家信息化部首席顾问andres kütt的一次采访中可能隐藏着解决难题最后一块拼图,他将这种紧密合作比作一种「集体大脑」并说道:「为了使集体大脑协调地运转,大脑的各部分之间需要能够传递信任」。 在1990年代的爱沙尼亚,这种信任一方面源于国家规模小,人们彼此间都相互熟悉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重获独立的喜悦和热情。但是这种信任同样也根植于「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仰和光荣使命当中,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市场化竞争纵有千般好,但却永远难以孕育这份信任。 注释: [1] rainer kattel & ines mergel (2019) “estoni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ission mystique and the hiding hand” — in “great policy successes” (edited by mallory e. compton and paul t. 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